五九年读 的追忆
的追忆
 五九年高考发榜之时,我在漳埔乡下调查老区老革命的事迹,打电话问妈妈,才知是分配到福建师院英语系。我第一个反应是:不去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高考前填第一志愿时,十四个栏目,填的全是北大复旦这类重点学校的新闻系和中文系。谁知心高才浅,被安插在我想都没想过要读的英语系。后来,决定先去报到,
再转系。走以前,一中一个老师曾说要给我四块钱,后来没消息了。一个阿姨曾说要给我一个洗脸盆,也没消息。妈妈还是凑了一些钱给我,大姑婆也给了我六块钱。到了厦门,我买了一个袖珍脸盆,还买了一张五块多的火车慢车票,就到福州了。到站后,就听到大喇叭在播我的名字,原来是小学同学潘健飞来接我了。我们找到师院外语系的接待站,把行李交给他们,就和健飞步行从火车站走到他在水部的家里。健飞和我本是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的同学。他是军属,后来却因为他爸爸的历史问题(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),哥哥提前从部队里复员,健飞也考不上大学了。
五九年高考发榜之时,我在漳埔乡下调查老区老革命的事迹,打电话问妈妈,才知是分配到福建师院英语系。我第一个反应是:不去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高考前填第一志愿时,十四个栏目,填的全是北大复旦这类重点学校的新闻系和中文系。谁知心高才浅,被安插在我想都没想过要读的英语系。后来,决定先去报到,
再转系。走以前,一中一个老师曾说要给我四块钱,后来没消息了。一个阿姨曾说要给我一个洗脸盆,也没消息。妈妈还是凑了一些钱给我,大姑婆也给了我六块钱。到了厦门,我买了一个袖珍脸盆,还买了一张五块多的火车慢车票,就到福州了。到站后,就听到大喇叭在播我的名字,原来是小学同学潘健飞来接我了。我们找到师院外语系的接待站,把行李交给他们,就和健飞步行从火车站走到他在水部的家里。健飞和我本是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的同学。他是军属,后来却因为他爸爸的历史问题(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),哥哥提前从部队里复员,健飞也考不上大学了。
 第二天,由健飞陪着,到了仓前山麦园路11号的外语系。我第一件事是找到系里管学生的林启福老师,要求转到中文系。他说了些什么,我忘记了。但我很知趣地拿了行李去我的宿舍和教室了。我是63级英专A班,全班有20人,约一半是印尼侨生。这20人到了四年后毕业时,少了7个人,其中一个转学,两个病退,四个被开除。被开除人中有原来的班长和团干部。这也差不多是我与共青团无缘的原因。我本来还想争取入团的,后来问明白入团必需请人家当介绍人,再按时向他们汇报思想,我就知难而退了。[右边的照片就有后来被开除的两个团干部。]
第二天,由健飞陪着,到了仓前山麦园路11号的外语系。我第一件事是找到系里管学生的林启福老师,要求转到中文系。他说了些什么,我忘记了。但我很知趣地拿了行李去我的宿舍和教室了。我是63级英专A班,全班有20人,约一半是印尼侨生。这20人到了四年后毕业时,少了7个人,其中一个转学,两个病退,四个被开除。被开除人中有原来的班长和团干部。这也差不多是我与共青团无缘的原因。我本来还想争取入团的,后来问明白入团必需请人家当介绍人,再按时向他们汇报思想,我就知难而退了。[右边的照片就有后来被开除的两个团干部。]
不过,我跟班上大部分同学还是很好的。侨生们一般比国内生单纯, 坦率。我的最好的朋友是一对后来成了夫妇的文宗和箴英。文宗是厦门人, 文娱委员。四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听到《草原之夜》这首歌,我就想到文宗当年唱这首歌的翩翩风度。59年到63年间是中国所谓自然灾害的时期,物质很不丰富,但政治上相对放松。我们有下乡劳动过,但很少整来整去。系里周末经常有舞会,弹电吉它伴奏的大都是本系或外系来的侨生,跳舞的有本系或外系来的靓女。我曾经慕名去看过一回,但马上就知道去那种地方要穿戴整齐,打扮得体。连一双皮鞋都没有的我,自惭形秽,从此就不再去了。不过,我却也找到属于我的角落:我的书桌。五九年国庆大庆的五天假期,我向一个老师借到一架二十年代的英文打字机,一连五天,从早到晚,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学打字,严格的十指指法,touch
type。带子打不出颜色了,用煤油沾沾,继续用。后来,打字机带都有破洞了,就去买了复写纸,垫着打。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的英文诗,我就是这样一首首打到我的活页纸上的。虽然一年级我英语是从字母学起的,到了四年级,我的笔语成绩应该是班上属一属二的。我有志考研究生,但报名要经系里同意,他们不批。十五年后,到了1978年,我终于成了文革后第一批的英语研究生,到了厦门大学外文系完了我的研究生梦。[左边的照片拍于大学毕业前夕。我的同学林璨崎让我穿上他的西装,还给我打上他的领带。]
文娱委员。四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听到《草原之夜》这首歌,我就想到文宗当年唱这首歌的翩翩风度。59年到63年间是中国所谓自然灾害的时期,物质很不丰富,但政治上相对放松。我们有下乡劳动过,但很少整来整去。系里周末经常有舞会,弹电吉它伴奏的大都是本系或外系来的侨生,跳舞的有本系或外系来的靓女。我曾经慕名去看过一回,但马上就知道去那种地方要穿戴整齐,打扮得体。连一双皮鞋都没有的我,自惭形秽,从此就不再去了。不过,我却也找到属于我的角落:我的书桌。五九年国庆大庆的五天假期,我向一个老师借到一架二十年代的英文打字机,一连五天,从早到晚,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学打字,严格的十指指法,touch
type。带子打不出颜色了,用煤油沾沾,继续用。后来,打字机带都有破洞了,就去买了复写纸,垫着打。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的英文诗,我就是这样一首首打到我的活页纸上的。虽然一年级我英语是从字母学起的,到了四年级,我的笔语成绩应该是班上属一属二的。我有志考研究生,但报名要经系里同意,他们不批。十五年后,到了1978年,我终于成了文革后第一批的英语研究生,到了厦门大学外文系完了我的研究生梦。[左边的照片拍于大学毕业前夕。我的同学林璨崎让我穿上他的西装,还给我打上他的领带。]
再说说健飞, 他入大学没门,只好自己学医。历尽挫折,全家还曾被赶上山下乡。四十余年过去,他现在是福州市一位很有名气的坐堂中医了。“三指努力知分晓,两服争取见疗效”是写在他名片上的宣言。如果没有民间医学的这个宝藏,如果没有他的灵性和拼搏,他差不多就在那个制度下被压碎了。“还好有中医,”他曾心有余悸对我这样说。
燕南 记于 2002年4月4日
大学教育对人的一生有极大的影响。我的今天,其实仍跟四十多年前的这大学四年有关。毕业后,同学们各走天涯,很少联系。但我经常想起他们,尤其是班上的印尼侨生们。在那个特殊的“瓜菜代”时代,我们这些“国内生”们沾了不少光--或者说不少油,不少粮。每逢郊游,或其他活动,都是他们出粮出油出钱。他们还给我华侨粮票,让我寄给妈妈和弟弟(结果妈妈还是买了饼干寄来福州给我)。那时我体质差,怕冷。有一个同学(天雷)送给我一件夹克,另一个同学(杏恩)借给我一件毛毯。我一心想买一个打字机。东街口的旧货商店有一台1920年代出品的
Royal 牌的英文打字机,人民币七十块。我去看货看了好几次,告诉妈妈我想买。她变卖了几件家具,给我汇来四十块。一个侨生(杏恩)借给我三十块。到了毕业后我有了工资,想还那三十块。一问杏恩,才知道那三十块已经由另一个同学在毕业前夕悄悄代我还了(见文宗箴英)。这个英文打字机跟了我二十多年,直到八十年代“改革开放”后,在香港的另一个同学(璨崎)给我买了一个新的。
印尼民歌“星星索”是当年(六十年代初)在我们学校(福建师院外语系)常可听到的歌曲。东方歌舞团陈俊华在央视四台国际频道上的表演(影视文件见下),原汁原味十足。收录在这里,以推崇她的演出,并纪念当年的印尼侨生们和从他们那里听到和感受到的印尼风情。下面第二首“星星索”是
MP3 格式,不到 4MB,是另外一组歌手唱的,也唱得很好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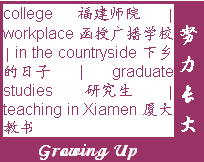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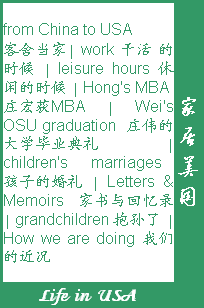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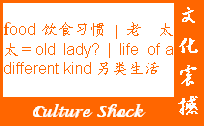
 的追忆
的追忆
 文娱委员。四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听到《草原之夜》这首歌,我就想到文宗当年唱这首歌的翩翩风度。59年到63年间是中国所谓自然灾害的时期,物质很不丰富,但政治上相对放松。我们有下乡劳动过,但很少整来整去。系里周末经常有舞会,弹电吉它伴奏的大都是本系或外系来的侨生,跳舞的有本系或外系来的靓女。我曾经慕名去看过一回,但马上就知道去那种地方要穿戴整齐,打扮得体。连一双皮鞋都没有的我,自惭形秽,从此就不再去了。不过,我却也找到属于我的角落:我的书桌。五九年国庆大庆的五天假期,我向一个老师借到一架二十年代的英文打字机,一连五天,从早到晚,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学打字,严格的十指指法,touch
type。带子打不出颜色了,用煤油沾沾,继续用。后来,打字机带都有破洞了,就去买了复写纸,垫着打。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的英文诗,我就是这样一首首打到我的活页纸上的。虽然一年级我英语是从字母学起的,到了四年级,我的笔语成绩应该是班上属一属二的。我有志考研究生,但报名要经系里同意,他们不批。十五年后,到了1978年,我终于成了文革后第一批的英语研究生,到了
文娱委员。四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听到《草原之夜》这首歌,我就想到文宗当年唱这首歌的翩翩风度。59年到63年间是中国所谓自然灾害的时期,物质很不丰富,但政治上相对放松。我们有下乡劳动过,但很少整来整去。系里周末经常有舞会,弹电吉它伴奏的大都是本系或外系来的侨生,跳舞的有本系或外系来的靓女。我曾经慕名去看过一回,但马上就知道去那种地方要穿戴整齐,打扮得体。连一双皮鞋都没有的我,自惭形秽,从此就不再去了。不过,我却也找到属于我的角落:我的书桌。五九年国庆大庆的五天假期,我向一个老师借到一架二十年代的英文打字机,一连五天,从早到晚,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学打字,严格的十指指法,touch
type。带子打不出颜色了,用煤油沾沾,继续用。后来,打字机带都有破洞了,就去买了复写纸,垫着打。拜伦、雪莱、济慈的英文诗,我就是这样一首首打到我的活页纸上的。虽然一年级我英语是从字母学起的,到了四年级,我的笔语成绩应该是班上属一属二的。我有志考研究生,但报名要经系里同意,他们不批。十五年后,到了1978年,我终于成了文革后第一批的英语研究生,到了


